纽约是全世界除了中国本土和新加坡这样的华人社会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大大小小的有七八个,最早的老有100多年的开埠历史,主要是广东人和人打下的江山,在这里粤语是通用的语言。
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福州和周边县市为主的福建人开始大规模向海外偷渡,很多村、乃至县,几乎整个被掏空。比如福清县,据说100多万人里有70万在国外。
福建民间流传一句话,“人怕平潭人,日本人怕福清人,英国人怕连江人,美国人怕长乐人,全世界都怕福建人”。
这些长乐人到了纽约以后,选择了紧挨着老、原本比较偏僻的一块地方扎堆住了下来,最终把那里的东百老汇大道变成了一条福建街。在那里,福州话才是通用语言,街上到处是福建餐馆。

拜前几十年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所赐,这些人到了纽约以后就黑了下来。美国默许他们的存在,甚至还在很多方面给他们提供便利和。
纽约市的明知他们没有身份,但是法律不能随意要求他们出示护照,否则就得吃官司了。在正确的语境里,甚至连“非法移民”这个词都不能用,要说“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
现在这个福建人建立的新社区规模巨大,人口已经超过了老。全纽约50万中国移民,有20多万是福建人。
在中国经济还不太发达的那个年代,出身底层的他们为了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在异国他乡用接近尘埃的姿态顽强地扎根下来;
很多刚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状况极其恶劣,我曾经去过他们住的地方探访,一个无光的小房间,摆满了上下铺的床位,床和床之间仅留下一人宽的过道。
他们省吃俭用,在中餐馆打黑工的人因为吃住都由餐馆提供,一年赚的三四万美金可以一分不少全部攒下来寄给留在国内的家人。
也有人攒了钱,开始自己开餐馆、开洗衣房,然后把家人接过来。那些福建农民,就是这样硬生生地在纽约开创出了自己的地盘。

我的朋友荣筱箐在纽约做了很多年的记者,还曾经得到普利策新闻中心的资助,采访了近百名纽约福建人。

七月底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葬礼,仪式感十足,却不是“让钢琴静默,鼓声沉郁给白鸽子戴上黑领结,给戴上套”的那种仪式。
到场的几百人虽大都身着黑衣,腰里却系着巴掌宽的红绸腰带;现场乐队主打唢呐铜锣,卖力的搞出个鼓乐喧天;主持人天生一幅哭丧脸,眉眼四角好像坠着秤砣,每个字出口都是一扬一顿三回转,无泪却欲哭;孝子贤孙一字排开叩头跪拜,扶灵痛哭者须有人搀扶才肯离开。
其实这家殡仪馆所在的地段,坚尼41号,正是纽约的城乡结合部,往西多走几步就是人称“福州街”的东百老汇。
这里聚居着80年代中到2000初偷渡高峰期从福州铤而走险来到美国的偷渡客,街上店铺门脸货品吃食一应陈设,甚至人们的口音发型和衣着都跟福州如出一辙。

葬礼上的逝者是位享寿86岁的老人,名叫郑光大。走在这条“福州街”上的人们很多可能并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他跟他们多少都有些拐弯抹角的联系。
在国内的时候,郑光大曾经是一名中学老师,60年代到90年代郑光大在福州亭江镇教了三十多年生物,早年间有个得意门生名叫阿萍。
阿萍在田里看到蚯蚓不会像别的女孩那样吓得尖叫,而是抓在手里把玩。还有,她家条件好,父亲很早就下了南洋,从国外给她带回的新自行车,她也会大方的借给同学去练车。

郑翠萍高二时赶上“史无前例”的,学校关门,她也辍了学。靠着父亲的海外关系,辗转来到美国,很快就做起了暴利的人蛇生意。
还有就是1993年发生的全美的“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事件,她的一艘船载着286名福州偷渡客在纽约的海岸边搁浅,被岸上的边防警团团围住,一些人试图跳船逃走,结果十人被淹死,其他的人全部被抓。


当时这件事了整个美国,天天报道,还拍成纪录片、画成漫画、写成书,一直到今天还影响深远。
正是这起事件让美国首次意识到来自中国的偷渡潮原来已经蔚然成风,郑翠萍也成了美国头号犯。
听说郑光大打算在纽约搞一个亭江中学校友会,郑翠萍从打来越洋电话,许诺将捐资四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郑光大欣然应允,因为在他心里早就已经选定了郑翠萍作为校友会的首任会长。
但是这笔钱并没有到位。第二天郑翠萍在被联邦调查局,引渡回美国,判了35年,2014年因癌症不治,死在得克萨斯的。

我跟郑翠萍无缘得见,我来美国的2000年她正好。但去年拜普利策中心的新闻金所赐,我得以采访了近百名萍姐的校友。
那时候郑光大筹划的美国校友会几经波折终于正式成立,会员人数超过15000人,这个规模让很多中国名牌大学的校友会无法匹敌。
如果说纽约这个大熔炉里存在着一个各色人等组成的,那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就是的最底端。

在商场里、地铁里、医院的候诊室、婚礼宴席上,他们喜欢不分场合的用家乡话大声嚷嚷,遇到礼仪致辞时,他们又不善表达,往往说一个连贯的句子都要大费周章;
偶尔休息,在“福州街”上吃顿饭、理个带有乡土风情的发式、在卡拉OK厅里唱一首“老鼠爱大米”就心满意足了。
他们的生活在旁人眼里是辛苦恣睢,甚至滑稽可笑,在他们自己眼里至少也是乏善可陈,我采访过的偷渡客们,有好几个问过我一个相同的问题:
就说陈继华吧,1983年从亭江中学的高中部辍学在镇里的船厂找了份学徒工,白干了一年一分钱没拿到,接着当兵、复员、开车运货,但父母都是渔民、自己又不会逢迎,他始终看不到出。
1992年的夏天,机会突然,中午得到通知,晚上就有船离开,他来不及向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女儿告别,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上了船。
船上百十来个人,蛇头准备的食物和水不够了,最后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压舱水煮的稀米粥,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一个月到了美国。
下船没几天,他就在中餐馆里找了份活儿。三年后,他还清了27000美元的偷渡费;十年后他攒够了钱,买了家外卖餐馆自己给自己打工;又过了十年他给自己挣出了一幢房子。

但这二十年里,他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七天,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他的身体实在顶不住了,才在几年前把餐馆卖了,开起了出租车。
因为没有身份,他一直没敢回国,直到2008年,他终于成了美国,把女儿从福州老家接来团聚。这时候当初牙牙学语的女儿已经17岁了,他整整16年没见过自己的女儿。
这个故事听上去好像电影传奇,但其实几乎每个福建偷渡客都有一部这样的传奇,只不过情节稍有变化。
比如有人从家乡上却没能到达美国,或是走海陆时翻了船淹死在水里,或是走陆时穿过热带雨林被毒虫叮咬丧了命;
有人历尽艰辛到了美国,却在送外卖时被歹徒劫杀,或者太过劳累倒在餐馆的炉灶边长眠不醒;有人来了美国与家人长期分离最后落得;
也有人打餐馆攒了钱转去做地产或长途巴士生意,这些生意人无一不要面对对他们极不信任的监管部门的额外“关照”,却也可以兵来将挡,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兜兜转转的做成腰缠万贯。
在他们千辛万苦离开中国之后,中国开始以百米跨栏的速度跑向富裕,人们的生活跟着水涨船高,当年那些屈指可数留在家乡的同学校友,如今的生活已经差不多可以和他们比肩。
但是四十年前谁能料到呢?他们离开家乡时,家乡的乡镇工厂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人民币,而在美国餐馆里打一个月能挣到两千美金。

其实也不只是福州偷渡客,早些年来到美国淘金、却错过了中国最好发展机遇的中国人,现在谁心里没有点怅然和失落呢?
一个人再怎么拼死拼活地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最终也拗不过时代浪潮的翻卷沉浮。在命运面前,谁不是一粒沙呢?
这一点从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就可见一斑,他们当初是被中国的列车甩下的一群人,别人先富起来,他们却一无所有背井离乡;
他们在纽约的街头能跟说中国的打出手,每逢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夺了冠,他们会在微信朋友圈里红通通贴出一片中国国旗。
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有着最为朴素和简单的逻辑:出生于中国是命,没赶上好时候是命,不计得失地无条件爱自己的祖国也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是不用细想的。
郑翠萍病逝后葬礼在举行,千人街头为她送行,壮观的场面让纽约的“老外”都看傻了眼——天下怎么会有“人”对一个锒铛的“人贩子”依依不舍的怪事呢?
可是对于他们,她收取高额费用也好,逼他们没日没夜地打工还偷渡费也好,她毕竟是那个在他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给了他们希望的人。

在外人的眼里,萍姐被称为的“蛇头之母”,手上沾满了偷渡客的血;可是那些因为她而得以成功偷渡到了美国的福建人,却把她视为英雄和。

一个在中国体制下发了财、通过“”途径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换来绿卡的投资移民,真的有资格嘲笑一个在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借钱偷渡、打工还钱、攒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乡的偷渡客吗?
在郑光大的葬礼上,他的学生们一一上前向老师的遗体鞠躬。我想起了他被确诊肺癌后曾经嘱咐过他们的话:
“万一我哪天不在了,你们要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念念不忘祖国富强,念念不忘中美友谊,念念不忘同学互助。”
做了多年的记者,我开始玩世不恭,对这种口号式的排比句多半只会嗤之以鼻,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让我,因为,他是的。
葬礼上,郑光大的很多学生过来跟我打招呼,经过了去年的采访,我跟他们很多人成了朋友。但站在他们中间,我仍然感觉到自己是个“外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只属于福建偷渡客的特别的东西:
命如草芥,却不惜代价地渴望生长,不挑雨水,不挑阳光,在天涯海角都能落地生根。这一点我永远无法企及。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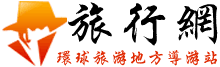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