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中国一类新药研发管线年爆发式增长,无论是新药申报的临床数量,还是新药批准的试验数量,增速都在20%-30%。上市批准药物的增速也突破性的达到了40%。“而这主要是由于整个行业存量的放量,且最大收益者是外资企业,因为毕竟他们在创新药物中的存量很多。”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吴淳在“2018浦江医药健康产融创新发展峰会”上一语点出现状。
在分析中国前20家研发储备最强的国内企业的在研管线后不难看出,中国药物研发仍然是以快速跟随为主,药物多为Me-too、Me-better,鲜有first-in-class。处于获批临床及一期、二期比较常见。
突破性创新现状和目前我国的仿创结构直接相关。一个明显的中国式现象,就是“热门领域扎堆”。有句玩笑话是“CAR-T疗法还没在中国上市之前,就已经从蓝海变成红海了。”
对比全球药企的研发管线领域布局,肿瘤药物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但在中国尤其为重,几乎占据了药企管线的半壁江山。其次是抗感染药物,虽然其用量明显紧缩,但美国药企在抗耐药性、抗病毒、抗细菌研发方面的投入仍非常大,中国却相当少。中国药企在一些热门领域、热门靶点投入了大量精力,据统计,中国前20家药企在研的VEGF项目达到22个,HER2项目15个,PD-1/PD-L1项目10个。如果统计全国所有药企,在研的PD-1/PD-L1项目将近100个。
创新研发除了前期靶点发现和化合物合成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临床。近年来临床研究需求激增,第一大原因就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从2018年底到2023年,国内需要一致性评价的药物保持在每年1500例左右。同时,新药的研发加速,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国内企业,对于临床试验的数量都将保持每年15%-20%的增长率;很多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也在增速,国内面临更多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要求。但实际上供给端常匮乏的,全国800余家临床试验机构仅有四分之一可以进行BE和一期临床,而能够满足中美双申报的机构不到10家。多数医院不够重视临床研究,床位提供不到20张。
在美国,不光有医疗中心与药企合建临床中心,一期到三期临床的病床数量在几十到上百张;还有一些临床研究中心,只接受一期或只接受二期和三期研究,均有15-120床,能从数量和质量上临床转换需求。“因此中国如何在临床中满足新药创新,以及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满足临床需求,是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吴淳表示。
未来中国医药研发创新要突破瓶颈、提升质量,真正进入第一梯队,“政策、人才、资金、生态、商业和创业文化”六大因素是主要推动力。吴淳详细介绍了前四大推动力将对医药创新产生的重要影响。
审批政策是推动国内研发力的第一道关口。从目前我国审批的时间点和要求来说,已经一定程度与国际同步。但审批制度可通过采用大数据、真实世界数据加快创新药物上市速度。
吴淳列举了美国一家著名药企一款免疫药物审批的案例,若履行美国FDA上市后承诺,采用传统四期随机临床对照试验证明该药物安全性的话,预估需要五年时间。《21世纪治愈法案》鼓励美国FDA采纳真实世界数据和替代终点,也通过了采信EMR电子病例的数据,结果该药物第四期临床用新的线个月之内达到了指标。时间节省了90%,成本节省了95%。这也是美国FDA考虑将来替代三期临床的方案,从成本来说,进一步加强了药企的创新。
药企大部分的资金和时间花在了三期、四期临床,如果缩短这方面的时间和基金投入,对创新药物增速将带来很大的帮助。但这不光要求临床设计和CRO的配合,还需要整个行业生态的搭建,包括平台数据的可利用性及真实性,整个行业的运算能力、算法和AI的支持。所以吴淳认为,“目前我们能做的,除了加强快速审批有条件上市之外,利用真实数据进一步加速医药创新的速度,是值得政策层面下一步考虑的话题。”
政策之中,除了国家药监局的职能,还有很大一块是医保。为什么中国不敢上市像CAR-T疗法等标价几十万美金的药物?因为没有太多人能用得起。这是中国目前医疗支付现状相对别国的不同。中国虽然是医药大国,但将近50%的医疗费用由个人承担。除2017年通过国家谈判机制进入医保的36个创新药,我国大部分创新药目前都是依靠个人支付实现商业的,进入医保对于前期投入很大的药企,或者小中药企来说,都是很大的引诱。如果医保能够采用动态谈判机制,或将吸引更多的新药进入。
中国的罕见病药物开发就受此制约。投资孤儿药需要考虑并非审批问题,而是获批上市后的支付问题。罕见病患者几乎不具备太多支付能力,也没有商保支持,因此有了治疗药物也是“叫座不叫好”。所以支付问题已经成为创新药发展很大的挑战。
中国医药医疗支出按P6%来计算,我国仍有提升空间。从医保和社保角度,不太可能完全支付创新药;个人集资支付的能力也太弱,因此只能靠商业保险。预估十年后中国健康险的支出会整体提速,已有很多健康保险公司或传统保险公司都把健康险作为下一轮的增长点,保险公司已开始考虑如何发展健康险(包括分为大病保险和报销型),如何更好地跟医院、医药公司进行数据对接,如何更好地加强他们在健康方面的结算能力。所以在供给侧方面他们是做好准备,以大量资金进入医疗市场的。
不光是在医药方面,医疗保险对医疗机构也做出了很多投资和贡献。吴淳指出,未来整个商业健康险会有长足的发展,而且其将是很多创新药可供医保和支付的渠道及支出口,为创新药、高价药的可及性带来促进作用。
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人才。有人才,才会有资金,才会使资金成倍地为生产力,产出结果。我国“千人计划”已经吸引了六千多名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从国外回到中国进行创业和创新。对于医疗产业来说,他们是排头兵,是基础研究、靶点发现到创新药物的最后落地,但吴淳,国内药企还应该在梯队方面做足两点:
第二是在研发和创新体系里,应提升R&D(自主研发)、BD(产品和项目拓展)、CD(公司层面并购)人才水平,并将三方面合在一起把握节奏,尽快实现创新突破。
的资金、企业自身的资金、创投和私募以及二级市场的资金,如何共同打造一个好的资金链条和供应链,创新每个环节的链条不会断呢?
第一,基础性研究投入,中国还比不上美国。体量上可能是现在只是其五分之一左右,投入也远远低于在美国。“基础研究不加强,我们一直将受制于人”,吴淳说,“没有新靶点发现,没有基础机理发现,没有创新模式治疗方式的突破,我们走不出仿创的步骤。”
第二,是药企本身的研发投入资金及临床试验数量,全球药企前五的研发投入是440亿美元,全球生物技术企业前五研发投入156亿美元,而五家中国大型药企包含恒瑞、石药、复星医药、上药、海正的研发投入为7亿美元。除了基础科研,同样反应了我国一期到三期临床储备不足。
第三,医药投资、融资规模近几年呈爆发式增长,创投达到120亿美元的水平。但由于仍处于早期,我国现在还没有太多专业性的投资,投资和投机的成分并存,相对短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吴淳列举了美国以公私合营的模式建立专项投资用于抗感染领域医学研究的案例。抗感染是医学创新的难题,并不像肿瘤那么热,但无论从医疗还是从整个社会卫生来说都是很大的难题,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BARDA)、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和惠康基金提供了4.5亿美元作为五年的投资额,资助了18个研究项目,医疗机构、科研机构也提供了很多专业知识。很多前期投资无法满足私募基金的要求,药企如何跟、研究机构合作进行创新性的突破,这也是资金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资金都是适合药物创新,也并不是所有药物创新都适合我们资金。
此外,港交所上市制度,企业资金达到15亿,有一项临床试验获批,有很好的机构投资人背书都能够上市。目前有十几家生物企业准备于港上市。而对标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247家生物技术公司,172家制药公司,73%上市公司尚未盈利,140家有收入但没有盈利,40家没有收入也没有盈利,这意味着其都是投入性公司,都是以长期融资进行进一步研发,扩大市场化才能达到盈利水平,整个实质是1.2万亿美金,是港交所所有的医疗健康企业8倍的体量。所以我们投资人哪怕从创投到私募上市以后,二级市场里面也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量支持我们整个创新投资,做到整个链条好的发展,这方面对投资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量和长期的布局。
药物的商业需要“政、产、学、研、资”联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需要建立技术流通、人才流通、资金流通的机制。
一方面,研究机构和医疗机构必须跟产业合作,这样形成一个科研到市场的。另一方面,通过临床前开发和安全性实验的药物需要重新再开发,药企可能将药物再转到科研机构,并投入资金二次开发。这个机制对于资金和技术的流通来说都是高效率的。
另外,PD-1药物Yervoy 2002年到2014年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的十年,可谓是生态圈里所有参与者努力的结构。2002年,陈列平教授在基础研究中发现具有肿瘤免疫反应功能的PD-1通,临床研究启动后被Medarex公司买进,由于二期临床中的突破创新,加速审批,BMS最后将其推向市场。企业、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缺一不可,各方合作才能够更好地提高率。
生物医药集群需要高校科研机构、生物科技企业、大型药企以及临床医疗机构共同形成。上海张江目前正在打造中国生物的体系,吴淳期待从中国上海出发,覆盖整个中国,都能产生很好的生态系统,为生物医药创新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态。
维基解密黄菊本文由来源于325棋牌 325游戏中心唯一官方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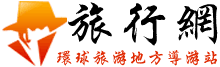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