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公园。我身后的向导一丝不苟地说:波士顿电影一英里之旅(The Boston Movie Mile Walking Tour,)就从我脚下开始,一囊括了《合伙人》、《无间行者》、《泰迪熊》和《心灵捕手》等多部电影的外景地。
不错,是张普通长椅,没有靠背,前面的池塘里也有一两只天鹅在游动。这让人想起电影里那个片断——满脸胡子的Sean以一句“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波士顿……”开头,然后对数学天才开始了布道式的关于艺术、女人、战争和爱情的经典对白。
这是个秋雨纷飞的早上,新英格兰的天气变幻莫测。长椅上写满了众多粉丝的留言,比如“Thank you Rip, the loves & memories”、“Love you Robin”等等。此情此景此刻,最适合怀念在那位2014年夏天过世、人人都喜欢的演员。

到达适逢哥伦布日前一天。我运气不错,礼拜天去Tihonet村参加蔓越莓节(Cranberry Harvest Festival)时天气放晴,阳光和煦。
你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人扎堆来加入这样一个乡村的节日。汹涌的人潮欢天喜地前来凑热闹,他们吃吃喝喝,欣赏乐队吹拉弹唱,然后坐拖拉机或者直升机观赏农场工人们在池塘中收采蔓越莓的壮观场景(工人把水灌进果田,让所有的蔓越莓果飘浮到水面,看上去像是一层覆盖在水面上又轻盈又美丽的绛色毯子,这真是个绝妙的采摘方式!)机器轰鸣,通过管子把无数的小果子送到岸上的卡车车厢。上了年纪的农场主就站在观光天桥上,殷勤地把新鲜的蔓越莓递到每个人手中。这些小小的红色果实并不如想象中甜蜜,可那是种带着清香的纯正乡野的味道,仿佛还带着蜜蜂扑动翅膀的嗡嗡声。
波士顿,或者整个都似乎历史回忆之中。在Prudential Center 50层的观景台上眺望雨雾迷朦中的城市,尤其会加深这种感觉。循着“之(the Freedom Trail)”红色砖石铺出的线,我走到Tremont街的一个拐角,就碰到位18世纪装束的小伙,正对着一群人激昂地讲着什么。一看到我们这些外国面孔,他赶紧整了整头上戴的三角帽,提高嗓门,继续刚才的:“我们不能再等了,已经有五个州加入了联邦,人不能再犹豫了……”说话间,一队同样戴着三角帽、穿着民兵服饰、背着长长滑膛枪的人马又从街上走过。十字口正好红灯亮起,他们向右通过人行道。旁边的下水道冒出了团团白色蒸汽,在迷离的水汽和细雨营造的舞台剧般的场景中,这帮古装民兵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列队在一辆辆克莱斯勒和道奇车面前通过,消失在横街深处。

这是“之”的一部分——战争的历史就这样每天在街头上演。这种历史感有如我在旁边的Omni Parker House酒店餐厅里喝到的蛤蜊浓汤一样浓烈有劲。人很怀旧。直到现在,我们还找得到四百年前首批移民登陆海岸的“普利茅斯岩”,也可以在普利茅斯种植园博物馆里重新领略17世纪初期的殖民点生活。他们还特地造了一艘“五月花二号”——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的复制品,一切都如当年旧制。唠唠叨叨的老水手、热情而善良的女仆还有自信满满的船长都能给你即兴讲上一段海上生活的艰辛与。是的,正如那些书中所述,男人们在船上签署了公约,上岸后又和土著Wampanoag印第安人订立了和平约定,然后是的拓荒岁月,第一个节……直到多少年后,和平不再。
列克星敦仍一如既往,静谧又迷人。这里也有黑斯廷斯公园旅馆(the Inn at Hastings Park)那样迷人又具传统气质的小酒店——进入它的走廊和房间,你就知道什么是时光倒流的感觉。最近几年,据说东亚移民的纷纷涌入已快速拉升了本地的房产价格。

小城里,标志性的急召民兵(Minuteman)雕像后面就是当年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战场之一。1775年4月日出后,约翰·皮特凯恩率领的英军先头部队和约翰·帕克的民兵武装在此。不想惹的双方起先都保持克制,可是万能的墨菲定律总归要发挥作用——一片混乱后终于擦枪走火。因为爱默生饱含的描述,列克星敦的第一声枪响也蜚声世界——实际上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只有天知道。在数英里外的康科德镇老北桥,则爆发了更为激烈的战斗。英军被击溃后不得不撤回波士顿。
此役战殁的英军士兵被敛葬于桥侧,墓前积满落叶,只有两面小小的英国国旗相伴。墓碑上刻着诗人詹姆斯·罗素·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写的如下字句:“不远三千里之遥,他们来此捍卫昔日,身死于斯:再也听不到万顷波涛之外,他们英国母亲的呜咽。”

爱默生,霍桑,梭罗和阿尔科特这几个美国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名字,都出身新英格兰。易莎·梅·阿尔科特的故居果园庄(Orchard)就在一条山间公的旁边。正是在这座房子里,阿尔科特和她的父母与姐妹一起生活,并写出了至今仍为许多人喜爱的《小妇人》。房中陈设一如其旧——这好比阿尔科特评价自己的小说:“如果它成功,我们的生活就是它成功的原因,我们确实就像书中写的那样生活”。卧室里,那张她写作的小半桌还在,桌上还有笔和稿纸,似乎一分钟前她还在那里伏案写字。
梭罗大概是他们中最特别的一位。他仅凭一本《瓦尔登湖》即赢得令名,也让那个他曾隐居两年又两个月的山间湖泊声名大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忘不了他在《经济篇》第一段中写下的那一句:“我孤独地生活着……在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以上,只靠着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

瓦尔登湖就隐匿在康科德镇以南约一英里的森林之中。我到湖边那会,沙滩上已经东一处西一处坐着好多人。小孩子们在开心地玩着皮球,大人们坐着吃吃喝喝聊着天。湖水清澈见底,有着鲜活的绿意——梭罗说,从远处看,它又变成蓝色。有人在湖中来回着独木舟,还有人在湖中游泳。翡翠般的湖面会在船和人的两边漾起肋骨般有序的波纹。这让想象中幽静冷僻的隐者之湖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热闹、其乐融融的游乐园。这其实也不是件坏事。梭罗来这里也是亲近自然,逃避嘈杂和他所认为的。
湖畔的沉思者宁可坐牢也不缴人头税的气概,其实堪比写出《白鲸记》的麦尔维尔的祖父托马斯·麦尔维尔在1773年12月16日参与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后者又岂是仅仅为了不愿多缴三便士的茶叶税?梭罗发明的Civil Disobiedience(不服从)是个颇值玩味的词。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就建在波士顿临近大西洋的港口边上,这位梭罗之后一百年的总统的许多场就在里边不停地滚动播放,他说的最多的词就是“”。这也可能是波士顿会用来定义自己的一个词(人们把热闹繁华的Faneuil Hall Marketplace称为“的摇篮”)。

湖边小径通向一百五十余年前梭罗故居的遗址,现在已然是一片荒墟,只有乱石两堆——也许真是当年他双手从湖边抱上来的那两车石头呢。已是仲秋,森林中红红黄黄的叶子四处点染,柏树和松树还是苍翠欲滴。鸟鸣山更幽,我听到的山雀或樫鸟的声音应该和梭罗听到的并无二致。
约翰不苟言笑,表情严肃地手扶船桨站在岸边沙地里的一条木船边上。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留着胡子,帽子、风衣、长裤和靴子无一不是梭罗时代的风格,这让他的确不太像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人。约翰扮演的正是梭罗的形象。“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把船划到湖上去”。听说我从中国来,他并不是很惊奇:“梭罗在书里好几次提到中国和孔子”,他说:“我对东方并不陌生”。
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个工作,他的嘴角终于掠过一丝不易令人觉察的笑意:“不,这并不是工作,这是一种生活。”然后,他挥动木桨在船舷上轻拍了几下。我理解了这种瓦尔登湖式的语言。

从荷兰隧道出来,纽约,确切地说曼哈顿的味道一下子就在眼前弥漫开来。不是每个城市都能让人在离开后还记得它的味道,但纽约恰好就是。百老汇、中央公园、时报广场、切尔西市场、纽约地铁……只要你在这里呆过哪怕几天,纽约总会给你留下一点不容易忘记的回忆。就像我从中央车站出来,随便瞥了一眼街边的旧书摊,就瞄到了一本寻觅多年的1973年版华莱士·斯蒂文斯诗集。
十几年前来纽约时,屡次放弃了攀登世贸双子塔楼的机会。直到后来有一天,它们在令我目瞪口呆的电视新闻里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轰然崩塌。所以这次我欣欣然就上了帝国大厦的顶上,在操着各种奇奇怪怪语言的观光客堆里俯瞰了一圈城区的全貌,同时想着晚上该去哪里打发时间(看个《妈妈咪呀》音乐剧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回到大堂,我荣幸地得到了一张登国大厦楼顶的证书——想一想,有那么多人排着长队,等着坐电梯到四分之一英里高的观景台上——你也许讨厌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构筑而成的森林景观,但摆脱的方向只有两个:要么水平;要么垂直——比它们更高。这确是件了不起的事。

恰当的高度能够带来恰当的愉悦。高架公园(the High Line Park)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公园的第三部分在三年前的秋天才开始对。多年废弃不用的铁轨边上,野草和得到精心养护的花木一起蓬勃疯长,公园步道的两边仍然是玻璃幕墙包裹的高楼。但是,你可以轻松漫步,高兴了还可以随便一坐下;你比街上的车辆和行人都高出十几米,你在他们之上;你可以看到哈德逊河缓慢流动的水面及河上的落日景象;你比任何不在这个由高架铁而来的公园里走的人都多出一段随意的时间,多一种谁也管不着的悠闲心情。
另一个公园虽然年头久远,但仍然有其不可的魅力——不用多说你也知道我指的中央公园。每次到公园逛总能碰到些新鲜有趣的人:歌手、乐师、占卜者、家、跳舞的人、甚至摔跤手。通常,他们的故事一点不比他们泰然自若表现出来的技艺差。五个来自非洲的艺人让我大开眼界,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鼓、跳舞,和过的其他舞者相互、对舞,从下午直到天黑,而他们需要的只是掌声和喝彩。

这次我碰到的另一位异人是布莱恩·法斯(Brian Fass),一个专门用老式宝丽莱相机拍照的人。他拍中央公园里的表演者,也拍来来往往的人。“我带着相机在公园里游荡,这正合我的天性。”自小生长在曼哈顿的布莱恩之前是个电影摄影师。2010年开始,他在中央公园发现了另一种生活——不再只是拍摄电影场面,不再受限于电影圈的等级森严,而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那些音乐人是布莱恩最喜欢的拍摄对象:“他们给这个城市绿洲带来了音乐和文化,一个接一个的美妙时刻令人陶醉”,布莱恩说:“很多人拍完照转身就走了,但我想在最近的距离上拍下他们最动人的一刻,然后把照片给他们看,给其他人看。我想让照片,没有声音的照片,也能承载音乐的灵魂。”
“我想把这个爱好变成一个事业。在我喜欢的公园里,拍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和全世界分享。” 布莱恩有自己的分享方式——他的网站、Facebook和Twitter账号。他正在筹划一个电影,关于中央公园里的这些音乐人,关于他在这个公园里找到的核心事物——生活。

换一个角度来看曼哈顿是必要的。搭乘Bateaux New York的游船,在月圆之夜漂荡于哈德逊河和东河,看那些亮着星点般灯光的高楼在岸上,如同中的巨兽般静默而缓慢地移动。你同时也不会闲着,可以和同伴把酒言欢,边上有乐师歌手轻歌缓弦助兴——这完全是塞纳河上那种风格的移植。游船会在像、布鲁克林桥和曼哈顿桥之间来回兜圈巡航,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曼哈顿桥上,从布鲁克林开来的夜班通勤地铁咣当而过,一长列明亮的车厢仿佛悬空滑过空旷而的河面,有如幻象。
“布鲁克林在1898年经市民投票并入纽约市”, “布鲁克林不插电之旅”(Brooklyn Unplugged Tours)的总监杰弗里解释说,“但实际上如果不并入,就可能会面临断水之虞”。布鲁克林的饮用水当时是由纽约市提供的。许多布鲁克林的“原住民”在此后选择离开,而更多的外来移民纷纷涌入填补空缺。半个世纪后,布鲁克林由原来的“地带”沦为麻烦不断的问题城区,以治安不好闻名全美。直到新千年后,布鲁克林才迎来新的转机——大批艺术家和设计师进入这里,个性鲜明的种种工作室、设计店、餐馆、酒吧和小书店令布鲁克林摇身成为新的多元时尚文化生活重镇。

杰弗里带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威廉斯堡北6街163号的Spire Lofts公寓,由原来的St. Vincent De Paul而来。整体结构完全保留,十字横梁、圆拱窗、红砖墙等等都没有改动,只是把原有空间改成了舒适的套房(带阳台2居室的月租要5500美元!)。但如同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一样,来的人多了,地皮租金就开始疯涨,“艺术家在撤出”,他摇摇头。
靠近东河的北3街聚集了到布鲁克林不可不访的几个地方:“最好吃的早餐”Egg餐厅、Mast兄弟手工巧克力店和布鲁克林艺术图书馆。2006年,斯蒂文·彼德曼(Steven Peterman)和肖恩·朱克(Shane Zucker)发起了手绘项目(the Sketch Project),布鲁克林艺术图书馆是现在的旗舰图书馆。不管你是画家、插图作者,还是涂鸦爱好者,或者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你都可以到这个图书馆,免费翻阅这里的绘本。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就花25美元买一本Moleskin笔记本,画下你的喜爱的任何事物——世界,生命,旅行或者任何奇思妙想,你的这本手绘集就会加入书架上的二万多册绘本(同样由其他来自全世界的人创作),供其他人——这些手绘还会定期去各地巡展。
“你看街上的涂鸦,” 杰弗里指着街对面车库门上的彩色山羊涂鸦画对我说,“这面墙有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间由一位涂鸦师使用。期限到后,别人可以把旧的画覆盖,画上他自己的作品”。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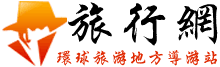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