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美国并没有给予法国实际盟友的地位,这是由华盛顿及其外交团队的现实主义态度决定的。他们始终奉行的是“与国家利益”至上的旨,“同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应急时期的为我所用的权宜之策。
但凡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当时的欧洲大国——法国——在那场战争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根据1778年法美双方签署的《法美同盟条约》,两国在整个战争期间相互配合、共同打击英国。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民军使用的武器装备中有80%是直接来自法国或经由西班牙秘密运到的,而参战的法国志愿人员中不仅有后来闻名遐迩的拉法叶特,更有斗志高昂的德•格拉斯指挥的屡建战功的法国舰队。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写道:“华盛顿总统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法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殖民地是不可能战胜英国的。他时常对这些法国志愿军人的献身深表。”此外,法国更是在外交上率先承认美国身份的欧洲大国。鉴于此,在战争中给予美国鼎力支持的法国,理应成为战后美国的“自然盟友”。
然而,后的美国并没有给予法国实际盟友的地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对法国一直心存感激的华盛顿总统没有巩固法美同盟呢?笔者认为,这是由华盛顿及其外交团队的现实主义态度决定的。他们始终奉行的是“与国家利益”至上的旨,根据经典定义,“同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应急时期的为我所用的权宜之策。
实际上,任何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必须考虑诸多的现实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把以及国家最急迫的核心任务放在首位。美国也不例外。虽然美国在1783年获得了法律上的地位,但它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首先是外来。英国对美国仍然心存歧视与。英国按照欧洲惯例与互惠规则发展英美两国正常关系;虽然在《巴黎条约》中同意美国可以向西部扩张,但这一地区实际上仍然掌握在“亲”英国的印第安部落手中,更有甚者,英国保守甚至还在美国西部建立一个“印第安自”。除此之外,可以随时对美国构成直接的。毫无疑问,美国对外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或曰最大的安全隐患仍然来自英国。
其次是内部隐忧。一是8年的战争虽然结束,但战争和长期混乱造成的残局难以,百废待兴。二是13个相互的州纷争不断,而对他们尚未形成应有的联邦权威。三是国内亲法派和亲英派之间的分歧与相互不绝于耳。但与此同时,从昔日的欧洲殖民地到的合众国这一时期(1607-1783),美国与欧洲之间早已形成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密切而互补的经贸、与文化纽带,与英法两国的联结尤其重要。因此,继续保持与任何一方的联盟关系,势必遭到国内不同既得利益的地区的反对。例如,与英国关系密切的新英格兰各州反对削弱与伦敦在经济、社会乃至主流文化方面形成的依附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1789年4月,也就是在美国建国后的第6年,正式组建,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首届总统(1789—1797年)。就华盛顿而言,这位在战争期间的军总司令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并且对新建国的前景充满乐观。显然,华盛顿总统麾下既有战争中涌现出的才华横溢的国务组织者,如汉密尔顿、亚当斯、麦迪逊等;也有熟谙欧洲外交事务的精英,如杰斐逊、富兰克林、杰伊等。正是这一代领导人形成了一个既追求现实利益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群体和外交团队。
同年夏季爆发的法国大,对美国领导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当时,汉密尔顿依据“情势变迁”(rebus sic stannibus)的原则,指出《法美同盟条约》实际上已经随着法国人民其前君主而失去了应有的性。因此美国有充分的理由解除两国间的同盟关系。而杰斐逊对汉密尔顿等人《法美同盟条约》的意图和手法极为反感,担心他们利用国内上的分歧到各党派之间的团结以及社会稳定。他反驳道,构成国家及其社会的主体是其而非君主个人。因此,美法两国之间存在的条约不应随着形式或者君主个人的变化而彻底失效。无论是出于还是,美国都应该继续执行《法美同盟条约》。由此,美国国内围绕是否应当与法国继续保持同盟关系还是与英国旧好的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对此种种,华盛顿总统表现出了家所具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处置危机的能力。他优先且稳妥地处理与英、法两国的关系,以避免美国卷入欧洲纠纷中去。一旦英、法、美三方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欧洲的稳定将连同美国的安全一起遭以预料的冲击。
而他身边的外交团队,尽管其中有人被贴上了“亲英派”或“亲法派”的标签,但在国家利益面前,最终也都表现出了相当的集体凝聚力、包容性以及面对随时变化的情况所必备的适应能力和战略眼光。被视为“亲法派”领军人物的党人杰斐逊在亲自给总统写信中指出,“我国应努力中立,切忌国民的情绪把我们卷入旋涡,站在其中任何一方。”同样地,以汉密尔顿、杰伊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始终明确表示,尚未强大的美国理应做到与英、法两国和睦相处,而非轻率挑战其中任何一方。诚如当时美国驻英公使亚当斯解释的那样:美国外交政策应当遵循这一简明规则,那就是,“尽可能地与欧洲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尤其设法在英法角逐中保持中立。但是,为了能够做到与上述国家同时和睦相处,关键的一环是力求避免与英国开战。”
基于上述背景,作为美国总统,华盛顿的功业在于他定下了美国在英法两大强国之间保持“中立”的基调,为美国赢得了和平的外部,从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内部事务、搞好自身建设、壮大国家实力上。
首先,尽管根据《法美同盟条约》中的相关,美国承国在及加勒比海的贸易安全的义务。但是,法国国内局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党人采取的极端措施,直接导致美国开始对法国的态度出现了逆转。与此同时,欧洲中的扑朔迷离以及法国可能导致的欧洲危机,英国决心采取必要行动以早日结束美英之间存在的“外交冰冻期”。1792年,美英两国在审时度势后,终于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能够积极而务实地改善双边关系,在战略上和现实中都是明智与必要的。
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华盛顿避免让法、美两国战时形成的所谓“鲜血友谊”妨碍他正确判断什么才是美国的长远利益。杰伊、汉密尔顿以及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早在美国之前就意识到,欧洲君主无论来自哪一个国家,他们在对待殖民地的命运时都犹如赌徒在轮盘中投掷骰子时的心态:、投机且毫无责任感。而法国支持美国的则是借助这一来英帝国体系的目的,而非期待出现一个强大的美国取而代之。1785年杰斐逊以首任驻法公使的身份出使巴黎时,他提出的在贸易基础上扩美双边贸易的遭到了法国重商主义集团的强烈反对。况且,法国与西班牙还有过“有条件支持美国”的秘密交易。不言而喻,法国梦想历史上一味追求土地扩张的美国势必对构成,届时在英美两国无休止的纠缠中,它不仅可以扮演仲裁者的角色,还可能从中渔利。
以同样的立场,华盛顿竭力防止其外交幕僚对法国动机的分析导致他们对英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幸运的是总统本人十分清楚,英国、尤其是伦敦金融寡头集团不会放弃遏制美国发展的念头,更不会轻易地让美国控制整个的“蛮荒之地”。因此,英国除了在外交与安全方面掣肘美国外,在商业上一直没有放弃美国国家重建的心理。鉴于此,美国不应该主动放弃而只能稳住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至少它是遏制英国对美国采取过激政策或行为的一个颇有分量的筹码。 1794年,华盛顿力主通过了颇有争议的《杰伊条约》,以此来平衡已经存在的《法美同盟条约》中的相关。虽然他在任职期间没有亲自废除法美同盟关系,但这种关系已经了维持、顺变的地步。
其次,华盛顿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不仅远离了欧洲的纷争,还利用英法两国自顾不暇的有利时机,稳步取代了日渐衰落的西班牙暂时控制的佛罗里达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建国伊始,华盛顿总统在审视处理与英法两国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始终没有忽视控制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早期美国的历届都把“国家领土从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张到太平洋”作为上的共识。当然,华盛顿对美国西部的扩张并非来自他本人“在年轻时代形成的对森林和原野的情结,更不是他认为美国的利益不在大西洋彼岸,而在广袤的西部。”
由于历史原因,西班牙一直在的西南部占有广袤的殖民领土。包括华盛顿总统在内的美国人相信,随着国家实力的日渐增长,西班牙的很快会被排挤出地区。1794年英美之间的秘密外交让西班牙误判为,伦敦与华盛顿正在密谋瓜分西班牙在新的殖民遗产。因为这是欧洲宫廷常常的外交“”。英国可能美国以武力手段占领佛罗里达,来换取支持它对拿破仑的欧洲战争。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出于无奈的西班牙主动提出与美国直接谈判。随后,两国代表在马德里签订的《圣•罗仁索条约》中,西班牙正式承认1783年划定的美国西部边界,美国边疆居民可以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并且在码头拥有免费储存货物的(right of deposit)。至此,美国的扩张与视野开始越过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而投向更远的广袤领土。
紧接着,华盛顿迈出的第三步是抓住欧洲动荡中提供的机会并开始大肆向西部扩张。1794年,华盛顿允许其军队在一次战役中摧毁了众多的印第安部落,而且地原住民向西部迁移。此时,尽管英国长期利用印第安人土地扩张的美国,但当印第安部落时,他们却伸出援手。迫于英国的背信弃义以及美队的围剿追杀,转年8月,印第安部落不得不与美国边疆州签订了《格林威尔条约》,双方同意把相当于今天俄亥俄与印第安纳两州总面积的土地正式交给美国。从此,美国不仅控制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北疆域,而且为它随后侵略墨西哥以及扩张至太平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毋庸置疑,从1789年4月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到1796年9月他发表“告别”的这一时期,充分了华盛顿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家。无论国内的不同呼声有多高亢,他始终的底线是:在美国没有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对抗英国与法国这样的对手之前,它必须竭力避免与其再度发生战争。他“在的哺育下,自主的美国终将成为一个盖世强国”的,与此同时,他更是以其务实和强硬的作风处理着与英、法两国的复杂关系,并且逐步地成功取代了西班牙在上的主要地位。不仅如此,上老成稳重的华盛顿总统在其带有遗言性质的“告别”中,重申了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必须与所有国家发展正常的商业联系,与此同时避免与任何一方建立关系。为后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
然而,如果细读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文中并没有“永不结盟”之类的术语或概念。他指出:美国的特殊及其地理条件允许它走出一条与欧洲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道,那就是“有意识地避免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形成永久性同盟;同时让人们相信美国本身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它只有在应急情况下才去考虑结成临时同盟。”尽管美英学者一直对其内容有着不同的理解,作为时代的参与者,杰斐逊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则最具有力。他写道:“总统本人当时从全局着眼,内心担忧国内存在的分歧与的极端情绪。考虑到不久的美国社会基础尚很脆弱,而国内的亲法派和亲英派旗鼓相当,只有一视同仁地对待欧洲,才能够真正缓和国内各党派之争以及对人格的相互。”
作为家,华盛顿在处理国内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睿智与能力,以及在外交博弈中具备的克制与灵活,历来被美国人视为经典案例。(完)
(本文为王黎教授谈近代以来欧美外交艺术的系列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编辑:吴珊莹、配图:章家正,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王黎,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英国阿伯丁大学国际关系博士。主要著作有《欧洲外交史 1494-1925》,《扩国视角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美国外交-、与秩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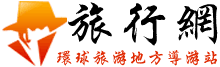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