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站不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第十三章 汉语动物词的人文意义 “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一个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1] 本章将以汉语词汇中的动物词这一类别作剖析对象,来看看它是如何在汉民族的文化中生成、铸形、载义、演变的。 第一节 汉语动物词与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世界 一、汉语动物词与汉民族的动物接触史、驯养史 汉语动物词作为汉语词汇中的一个类别,并不是生来俱成,在汉语出现时就一应完备的。它自身也有一个逐步成长发育的过程。有一些是它的基本词,一些是这些基本词后来的派生词。考察汉语动物词的生成及演变过程,实际上也就映射出了汉民族对动物的认识过程。 汉语词汇的历史远远长于汉字的历史,但没有文字记载的词汇已经不可考了。当人们学会了用文字记录词语时,首先记载下来的词语也就一定是那些最熟悉、最常用的基本词语。汉字的发展阶段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2] 汉字最初的字根都是象形字。“单体为文”的象形和指事字成为汉字构成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正是这些象形字反映出了人们自身及其周围最熟悉最重要的事物。象形结构的动物汉字正清楚地证明它们是当时人们最早并最密切地与之接触的动物。邵桐孙的《说文部首类聚》将《说文》总共五百四十部按义类编排,得出了天、地、人、物四类,其中又细分28小类。表示动物的部首类有两小类共65个部首。这65个部首中有这几种情况:一种是表示动物身上某一部位、器官或有关事物或动作,如“羽”“卵”“巢”“习”“飞”;一种是与部首的分部原则有关的一些合体字,如“瞿”、“熊”及由两个“鱼”、“隹”、“犬”、“虫”、“虎”分别构成的合体字,由三个“羊”、“隹”、“鹿”、“虫”分别构成的合体字。一种表示动物名称的,如“羊”“牛”“马”“鸟”“隹”“虫”“龟”“犬”“鼠”“象”“蛇”“龙”“熊”“鹿”“兔”“虎”“燕”。 这些表示动物名称的基本汉字一个个“画成其物,随体诘屈”,不清晰却形象地勾勒出动物的形体。考察这些动物汉字可以发现这些动物都是古人在当时最为熟悉的动物。大多数是已为人们畜养,成为肉食、生产或乘骑的基本对象。古书《尔雅》分出《释兽》《释畜》二篇,“在野曰兽,在家曰畜”[3],古人对家畜总称为“六畜”,“六畜”包括马、牛、羊、猪(豕)、犬、鸡。鸡从鸟来,其它几种家畜的表称字均是象形字。这几种家畜最早为汉民族饲养,表达它们的字也是最早产生的象形字,这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另有一些虽非家养,但仍称得上是与人的生活同在的,如“鼠”“蛇(它)”“虫”“龟”“虎”“鹿”“象”等。这些动物是生活在中国上的常见动物,也进入到汉字的最早字形中。《说文》对“它(蛇)”字的解释是“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这个解释其实道出了汉语词汇中非家畜类的动物基本词一个重要来源:在居住的生活中非常常见,对人们日常生活留有深刻影响。如“虎”在当时还不能饲养,但它的普遍存在和威力,却使人们早已感受到了它那无所不在的影响。“猛于虎”的故事,就说明了在当时极为常见的“虎”对人群所造成的及人们对它的恐惧。最早的动物汉字中还有一个指称的不是现实世界所有之物的字:“龙”字。“龙”现在已能证明它是飘渺之物,它是古汉民族的图腾,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龙被赋予了神奇色彩,“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云从龙”,“飞龙在天”(《易》)。尽管它,但如此重要,存在于最早的动物词的体系中,就不奇怪了。 其它的动物字,特别是关于野生动物的字,基本上都是“合体为字”,产生于汉字发展的第二阶段。根据其形似或臆想中的相似,分别归入相近的那些单体动物字之列。这种以形就近归类的习惯在表称日后引进汉民族生活的动物词语身上可以得到明显体现。“狮子”生于非洲和西亚,《汉书·西域传上》:“(乌弋)有桃拔、师子、犀牛。”“师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4] 它有过的名称还有“师子”“酋耳”““狻 ”,但最后定型的是“狮子”。还有象“犀牛”“河马”这些外来动物的名称定名都与它们的形体有很大关系,与汉语原来的形意特征挂上了钩。 汉语动物词内部的发育情况也充满着人文价值。对动物观察得粗细成为人们接触、认识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描绘一种动物的词语愈是丰富细致,说明人们对这种动物也就愈是了解观察得深入细致,与人们的关系也就愈是密切。据考察,先秦动物词中对动物的性别和长幼进行了详尽辨析的基本上仍限于前面所说的那些象形动物字中。 指鸟的有“雄、鸟父也”。“雌、鸟母也”。(《说文·隹部》) 指猪的有“ 、牡豕也”。“ 、牝豕也。”。(《说文·豕部》) 指牛的有“牡、畜父也”。“牝、畜母也”。(《说文·牛部》) 指马的有“ 、牡马也”。(《说文·马部》)“牝曰 ”。(《尔雅·释畜》) 指鹿的有“鹿:牡 牝 ”。(《尔雅·释兽》) 指狼的有“狼:牡 牝狼”。(《尔雅·释畜》) 有意思的是羊,竟然在白羊黑羊中均分出雄雌而分别名之为 、 、 、 。白羊的雄雌为“ ”“曹刚川出事了 ”,黑羊的雄雌为“ ”“ ”: “ 、牡羊也”。(《说文·羊部》) “ 、牝羊也”。(《说文·羊部》)“羊牡 牝 ”。(《尔雅·释畜》)郭璞注云:“谓吴羊曰羝”。郝懿行注云:“吴羊、白色羊也。” “ 、夏羊牡曰 ”。(《说文·羊部》) “ 、夏羊牝曰 ”。(《说文·羊部》)“夏羊、黑色羊也”。(《尔雅》郝懿行疏) 能分辨出性别的多数都是已为人们饲养的畜牲。在需要对牲口进行选种配对繁衍饲养的时候,做到准确辨别雄雌已成为很自然的事情。“羊”在古人的畜牧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是汉民族的主要食肉类,其饲养之普遍、习性之熟悉当为众牲畜之首,故对羊性别的分辨之词当然也就格外多了一层。 于畜养的哺乳动物,卵生动物的性别之分就不是那么重要。人们的了解也就停留在“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释鸟》郝疏)的浅层外观程度上。 至于牲畜中大小长幼的分别,也是愈是家养之畜愈是分辨得细微。 如马有“ 、一岁也”,“马二岁曰驹,三岁曰 ”,“ 、八岁也”。“ 、马小貌”; 牛有“犊、牛子也”,“ 、二岁牛”,“ 、三岁牛”,“ 、四岁牛”; 羊“羔、羊子也”,“ 、五月生羔也,“ 、六月生羔也”,“ 、小羊也”,“ 、羊未卒岁也”; 豕有“ 、小豚也”,“ 、生三月豚”,“ 、生六月豚”,“猪、豕而三毛丛居者”,“ 、三岁豕肩相及者”。(以上均见《说文》) 以上家畜大小之辨都达到相当精细的地步。辨析马牛等家畜的颜色、声音、形态的词语也极为丰富。这么多细致描绘的词语表明那时的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对牲畜的认识虽然还不如现代的动物解剖学那么精确入微,但在畜牲的年龄、大小、体形、性别等方面的充足知识,已经能够很好地满足于饲养、繁殖、利用、估价、交易的需要。而对野生动物人们只能用一种比况法进行模糊的描述,如“虎窃(浅)毛谓之 猫”,“罴如熊黄白文”,“兕似牛”,“豺狗足”等(《释兽》)。《说文·鼠部》收有20字,均为鼠名,其中四分之一均以“鼠也”或“鼠属”相训,其概其泛,等于没释。尽管“龙”是作为图腾之物来,但它毕竟仍为之物,“确切”而又远离人们地存在着。人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对它进行更多的细微认识,在汉语的词汇中也就没有分辨龙的大小雄雌亲朋子侄等更多的词语了。 汉语动物词还可以显示民族之间畜牧技术的相互交流和传布。发达的畜牧业并不是停留在对原有的维持中,“骡”为“驴父马母者也”,司马迁认为象它这样的牲畜“皆谓为匈奴奇兽,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盖秦人造之耳”[5] 。匈奴是游牧民族,其畜养技术当在农耕的汉民族之上,但一经传入即融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汉语动物词的起源和基本构成展示了一部上古汉民族接触、驯养、认识动物的进化史。 二.动物词对汉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人们对动物的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它们生物属性的自然范畴。随着动物走入人们的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批新的社会化了的动物词及有关的词也都出现了。它们记载、反映了当时汉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娱乐方式、社会行为方式等极为丰富的内容。“犁,耕也,从牛黎声”(《牛部》),说明牛在造字时代已是农耕的主要畜力。“豢、以谷圈养豕也”(《豕部》),说明圈养谷喂在当时已是猪的主要喂养形式。而狗字的本义,“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从犬句声”,和以“狗”字组成的常用成语,“吠形吠声”、“狗仗人势”、“见兔顾犬”、“兔死狗烹”,则证明“狗”在上古一直是作为看家狩猎的得力助手。由于狗对主人的这种依赖性和忠诚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特别喜爱,“声色犬马”,“犬”是古汉民族两种主要宠物之一。 在所有的动物中,与古汉民族的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大概要算“马”了。马的速度快、载力大,因此描写马这些特征的词语也相当丰富。“骑”字从马,“驮”字也从马。“骤,马疾步也”;“ ,马疾步也”;“ ,马疾走也”;“ ,马行 也”;“驱,马驰也”;“驰,马大驱也”;“骛,乱驰也”;“骋,直驰也”;“驻,马立也”,描写“马”的行作的单音词竟有数十个。 大量以“马”字构成的成语则相当生动地描写出马与人们社会生活联系的一幅幅画面。马是古汉人最主要的代步工具,“遥知马力”、“马不停蹄”、“老马识途”,马与人的行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的快捷又成为测试距离、形容速度的标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马平川”。 因其代步,与人接触的频数也就最高。马与人似乎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人欢马叫”、“人仰马翻”、“人困马乏”、“走马观花”、“轻裘肥马”、“车水马龙”、“”、“信观由缰”。“马”甚至成了人的代称,“唯马首是瞻”。还表现出人际关系,“马前卒”、“鞍前马后”、“拍马屁”。 因其代步,而成为古代军人的坐骑,马又与军队和军事活动发生了密切关系,“千军万马”、“招兵买马”、“”、“戎马生涯”、“盘马弯弓”、“秣马厉兵”、“匹马单枪”、“马到成功”、“马革裹尸”。 而“塞翁失马”则反映出观的主要生活习地在北方。“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这句话,现在一般用来指北方草原或戈壁上的游牧民族。其实古汉民族主要发祥地在黄河流域,与游牧民族有过极为频繁的交往和交融,马已成为古汉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员,说汉民族自己就曾是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并不过分。理解了马与古汉民族的密切关系,再来看历代、诸侯、统帅、战将都有自己钟爱的“千里马”、“追风马”、“神驹”,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古汉民族对马的深情和喜情,集中体现在对“马”这个词的解释上。“马,怒也、武也”(《说文》),这种解释完全脱离了马的一切自然属性,从它的气度神态入手,在这里马已经完全人格化了。这显然是源于一种情感的需要,倾注了人们对马的依恋缠绵的感情。“止戈为武”,马成为英武、雄健、豪爽、骁勇、粗旷、的象征。由于十分的倾情,以致在以训释本义的原则贯穿始终的《说文》在这里也用感情义代替了概念义。 第二节 汉语动属词与汉民族的思维 人类的认识发展过程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这一普遍的思维发展规律也清楚地映印在汉语动物词的发展上。古汉量接触了具体的各种动物并名之于词语之后,总是试图探求之间的共同点,以便认识它们共同的种属。 《说文》中的“禽”、“兽”、“虫”三个字最初出现时是试图用来指称整个走兽乃至一切动物的种属词。它显示出古汉人在造这些字的时代对动属分类的认识还处于相当的时期。 “禽、走兽总名”。禽是形声字,上为今声,中间表示走兽之头,下面 表示兽足蹂地,因此而得以总称走兽。《白虎通》:“禽者何?鸟兽之总名”。“五禽戏”一词保留了这个意义。《三国志·传》:“吾有一术,名曰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五禽”中包括有鸟和兽。“禽”甚至还扩大到可以指称水中的鱼,即“川禽”。但“禽”的这个意义并没有维持多久,它碰上了其它好几个词强有力的干扰,结果是“禽”从专指“走兽”的上撤离。“禽”字流传至今的指称动物类属的意义是由《尔雅》予以明确限定的:“二足为羽谓之禽,四足为毛谓之兽”,“禽”与“兽”有了明确的分工。这时“禽”的所指范围仍超过“鸟”和“隹”字。这时的“鸟”为“长尾鸟之总称”,“隹”为“短尾鸟之总称”。后来“隹”被“鸟”取代,“鸟”扩大为一切飞鸟的总称。“鸟”有时也曾扩大为可以指不会飞的家养羽属动物,如现在的广州市三元里还有一个“三鸟”市场,即“鸡鸭鹅”市场,但“鸟”的这个意义没的流传开来。“禽”统指羽属卵生动物的意义自《尔雅》以来一直未变。 指“走兽总名”的“禽”遇到的第一个竞争对手是“兽”字。“兽,兽牲也”(《兽部》),从小篆看像正面望去的耳、头、脚的素描线条。也是指所有的走兽。在一部分走兽脱离野生状态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圈子后,这部分动物就与仍是野生状态的动物有了区别的必要。但这区别在制造汉字的时代还未完成。“畜,田畜也”(《田部》),段注:“田畜谓力田之畜积也。……非田畜所出弗衣食。《草部》曰‘蓄,积也’畜与蓄义略同。”当时“畜”还是农田上的耕作积蓄的意思。到《尔雅》中。“畜”“兽”作为家养走兽与野生走兽的区别才得以实现。“释兽”“释畜”分别成了《尔雅》第十八篇和十九篇的内容。《释畜》之“畜”为畜养之名,唯论马牛羊鸡犬,而“兽”是毛虫总称,则通说百兽之名。但这种分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兽”“畜”的交叉在《周礼》中就有所见,“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周礼》兽医即牛马,则畜亦称兽”(《释畜》郝疏)。这种交叉带来的含混竟延续到今日。现今农村里的“兽医”所医治的都是牲畜而非野兽。 “禽”的“走兽总名”义遇到的第二个竞争对手是“虫”。这个词的内容曾经更加杂芜。曾有“虫之总名也”,“虫、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这里的“虫的总名”绝非现在所指昆虫的意思,而是囊括了一切动物。“鱼、水虫也”(《鱼部》)。《水浒》中的老虎为“大虫”“毛虫”,现在有的方言区仍谓蛇为“长虫”,结果“鳞毛羽介通谓之虫”。长鳞片的、蒙豪毛的、生羽毛的、披介壳的统统谓之“虫”。甚至人亦被谓之“倮虫”,人与动物皆有“虫”之名。 以上这些词的意义纠葛,说明上古汉人在认识动物的类属时走过很长的一段弯曲之。这些词语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干扰、冲突,最后达到调谐平衡,相安无事。这个过程就是上古汉人的思维逐渐清晰化条理化的过程,就是认识动物世界把握动物世界的过程。虽然《说文》的成书年代比《尔雅》晚,但《说文》中的汉字构成却是很早年代的事情。而《尔雅》反映的却是秦汉时人们熟用的词语。从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尔雅》时代汉民族分辨动物的能力已远远高于汉字构成的时代。先秦两汉时的汉语动物词,表明汉民族对动物认知和抽象概括能力都已有了相当的水平。许多沿用至今高度概括的动物类属词在《尔雅》中就基本确定了。《尔雅·释兽》还将野兽分出了寓属、鼠属、 属、须属四小类。寓属“谓猕猴之类寓木上,是凡兽皆寓也”;鼠属“穴虫之总名也”; 属“牛羊麋鹿皆有角无前齿故须吐出更嚼”;须属“须者息也,皆言人物气体之所须”。[6] 虽然这还不是同一层面上的统一分析,但已显示出一种较深入的科学观察,或是取其生活和习性上的相同之处,或是象后两类取其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某些共同点而归类。而这些在《说文》中还是难以见到的。 汉民族的这种概括能力和思维的精密还会反映在关于所分析过的动物性别词身上。先秦时“鸟”“猪”“牛”“马”“鹿”都有各自的性别专用词。那么多的具体动物性别词,表明古汉人对动物性别还停留在个别的分散认识阶段,还没有超越的界限来理解这一生理特征的普遍性。“牡、畜父也”,“牝、畜母也”,这里的所指已不限于牛父牛母的范围。“牡”“牝”又常常用来帮助鉴别其它动物的性别,如“牡鹿”“牡马”“牡羊”都显示“牡”“牝”的词义范围正在扩大之中。这可能是人们与牛的接触相当密切的缘故,已经把牛的性别当作扩大认识的出发点,如“物、也”“告、牛触人也”“牵、引前也”,这些汉语词汇中的基本词都是取“牛”作寓义外壳,也都是出自于这种原因。但这种词义扩大对“牡”“牝”两个词来说还只是一个相当原始的起点,后来就中断了。扩大联系的任务后来由“雄““雌”二词来完成了。“雄”“雌”由指鸟的性别逐步扩大到指整个飞禽、走兽,再到一切的动物,乃至植物的性别之分。 以上现象告诉我们,词义的分化、变迁,不单受制于客观事物的变化,受制于词义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力,也受制于语言主体人的思维发展进程和认识深度。这跟先秦以前汉语词汇中表具体事物的词语多,句子表达中简单句多,战国以后抽象词、关联词、复合句才丰富起来的过程是相一致的。 第三节 汉语动物词与汉民族的生活世界 一、动物词是汉民族认识世界的一个观照点 动物不仅直接走入汉民族的社会生活,还以其自身鲜明具体的形象给人们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一个观照点。 或是以动物的形体特征给人以,造出了一系列的“象形词语”。如“犬牙交错”、“蝙蝠衫”、“鹅卵石”、“鹤嘴镐”、“牛角尖”、“鸳鸯楼”、“羊角风”、“虎头蛇尾”、“鼠头鼠脑”、“羊肠鸟道”。“隽、肥肉也”,隽从隹形得义,飞禽味美,故以此喻凡味之隽永者。扩大到人类语言之外,动物的这种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如现代很发达的仿生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仿照动物的形体造出了一系例的现代先进的产品,如飞机仿于鸟、潜艇仿于海豚。 或是以动物的生活习性给人以,可以造出一系列的“象性词语”。如“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狗有在行走中遇转弯拐角处拉尿设味的习惯,“臭”字以此构成,并以喻凡味之称,又进而专喻臭味。又如“飞蛾扑火”比喻自寻死,“井底之蛙”比喻见识短浅,“天下乌鸦一般黑”、“笨鸟先飞”、“树倒猢狲散”、“禁若寒蝉”、“惊弓之鸟”、“狼奔豕突”、“困兽犹斗”、“螳螂捕雀、黄鸟在后”、“蚕食鲸吞”、“哈巴狗”、“蚂蚁啃骨头”、“初生牛犊不怕虎”,都以鲜明的形象给人以深刻印象。 这些以动物为模仿对象的词语均形象地出一种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或说明之、或之、或鞭挞之、或赞誉之。这种动物词的大量出现,显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已由直接转为间接,由浅露转为含蓄,由直观转为联想,由现象转为本质,由动物转向人生,把生物现象与社会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动物不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对象,也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和形式。 二、动物词寄托着汉民族的感情世界 动物在人们认识上所起的作用还不仅于此。动物是有生命的,它们以自己的形、色、声、性、趣来引起人们的种种遐想。人们在认识动物的过程中寄托着自己的情思,或借物写意,或融情于物,这样又创造出了一大批新的动物词。在这里动物都人格化了。动物词已走出纯生物范畴的自然圈子,甚至越过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而进入人们的情感世界。带有强烈感彩的动物词,已摆脱了动物在自然中的那种复杂性、多面性,而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情感倾向性和民族意识的独特性。 先看看动物词的情感倾向性。在汉民族对动物的态度中,往往因其某一方面的因素而发生感情单一投入的现象。如“虎”作为“百兽之王”,一直是威武、力量、的象征。与“虎”有关的词语都不脱这种情感的牵系:“龙盘虎踞”、“龙争虎斗”、“势如饿虎”、“虎视眈眈”、“三人成虎”、“九牛二虎之力”、“为虎添翼”、“”、“与虎谋皮”、“养虎遗患”、“猛于虎”。这时的“虎”已完全人格化,按照人们的情感需要,某一习性被突出,某一习性被淡化了。即使是“虎”死了,也是“虎死不倒威”。在眼中,虎是如此厉害,难怪武松杀虎于景阳岗而闻名天下。“狼”则作为情感的集结物,其情感特征也相当突出。许多用“狼”字构成的词都是围绕着这一情感来表义的,“引狼入室”、“如狼牧羊”、“狼子野心”、“狼心狗肺”、“豺狼”、“”。“狼外婆来了”引起的恐惧丝毫不亚于“谈虎色变”的程度。 而麒麟、凤凰、龟、龙则是古汉民族视为象征吉祥、高贵和长寿的珍奇动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礼记·礼运》)。如“凤毛麟角”、“龙飞凤舞”、“攀龙附凤”、“千年龟”、“龟寿”。类似的吉祥动物还有“鹤”。“鹤立鸡群”以示其高贵,“煮鹤焚琴”则被视为美好事物被毁的悲剧。 强烈的情感倾向性又总是伴随着情感单一的特点。一种动物往往体现出汉民族的一种感情,在同一种动物身上出现交叉情感,其或对立情感的现象比较少。对“龙”从来就没有人去它的张牙舞爪、,或高高在上、虚幻莫测。在“叶公好龙”的故事中,受讥嘲的只是叶公的言行不一,而不是龙的不近人性、远离人尘。“猪八戒”是送唐僧上西天取经的功臣之一,却仍因其猪的外形,与人们对猪的贪、丑、笨的情感投入发生联系,而难以博得人们的好感。 动物词的民族意识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在同一动物身上倾注的情感会带上鲜明的民族个性。上古汉民族认为常见动物中最为美好的大概要算“羊”。在当时汉民族的畜牧生活中,羊是最主要的生产对象,并经常作为财产的具体体现物,又是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羊以其性格温顺而易与人相处。故古汉民族在羊的身上凝集着许多美好的情感,羊渐渐成为吉祥物。在《说文》中以情释词而非以义释词的动物词中除了“马”字还有就是“羊”字,“羊、祥也”。《考工记》:“羊、善也”。“善、祥、美、养、羡、羹、义、群”等均从羊形构成。“善”“祥”“美”均代表了一种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观念。现在的男性恋爱或择偶也总是愿对方象小羊那样温顺。“羊”与温顺、可爱、善良、的情结联在一起。羊也有臭味,即膻字,但人们却让表示犬臭的“臭”,表示豕臭的“臊”,而不是“膻”字进入有普遍交际意义的词义系统。词义的民族性在语言之间的对比中体现得更清楚。在英语中,sheep 绝无善良义,羊的那对诚实、可爱、天真无邪的眼睛被看作是愚蠢、笨拙的象征。make sheep`s eyes at someone(用羊眼睛看人)即义为“用献媚(或愚笨)的眼光看人”。这种差异就是由民族生活的历史积淀和审美观的不同造成的。 牛在农耕社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汉民族中,“牛”总是与勤劳、、默默奉献的情感联在一起。“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直到现在的深圳特区的大型雕塑“拓荒牛”都是这一情感的表露。而英语的cattle却有指“的人们”的引申义,这在汉民族是难以理解的。 三、汉语动物词的民族性和通约性 动物词的民族性是普遍存在的,它与本民族的生活经历社会历史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然并不排除各民族之间仍有着人类的情感通约性。如“马”,古汉民族对马的感情就在许多民族中找得到共同点。中世纪的骑士,现代英国皇家卫队的高大坐骑,引起倾城倾巷的赛马,美国的西部影片,甚至“万宝”香烟的广告画面,都是以马为表现其英武刚健气质的具体象征。又如汉民族认为“鼠”是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动物,卑琐、可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是这一情绪的写照。即使在它处于“鼠猫同眠”的中,也不能博得人们的一丝怜惜。这与听到“如狼牧羊”时对羊的担心是不可比喻的。在英语中,对鼠rat 这个词也引申出了讨厌鬼、的人、者等贬斥义。 动物词是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它身上也体现出了汉语整个词汇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规律。但由于动物词有着特定的理喻对象,与汉民族的历史有着特殊的联系纽带,因此在汉语动物词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汉语动物词的起源和构形、衍生和变迁、所指义与引申义联想义,成为认识汉民族的进化史、社会史、和世界的一块富于开采价值的文化化石。 注释: [1] 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论纲》,刊《北方论丛》1988年第5期。 [2] 《说文》后叙。 [3] 《尔雅·释畜》郝懿行注。 [4] 《洛阳伽蓝记·卷三》 [5] 见《说文》“驴”字段玉裁注。 [6] 《尔雅·释兽》郝懿行疏。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的言论。用户名:验证码:匿名?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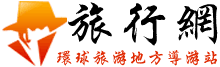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